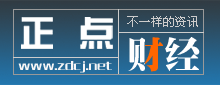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ͨÛ�r���҂���ô�k��
���ڣ�2012-07-27 00:00:00 ��Դ�����W
���� �P��˹���x���B�̲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vʷ�W�����᠖������ɭ(Niall Ferguson)7��20���ڡ����ڕr�l���uՓ���·Q�������ؔ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˽�˲��T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ұ،�����ͨÛ�A�ڼ�����Ψ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ڮ������Р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ʩ���w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Ŀ֑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Փ����ԭ�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20���o70���ĩ������80������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ƌW��(�������W)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ؔ�����ߵĴ�ӑՓ���˸е��چ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傃ʲôҲ�]��ӛ����ʲôҲ�]�W����ͬ�ӵ��u�rҲ��ȫ�m���ڽ��յĮ����P��˹���x�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h��Ը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o3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`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1936��s����÷�{�¡��P��˹(John Maynard Keynes)����ͻ;������͘I�����Ϣ��؛��ͨՓ��֮���W��Փ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Ҳδ�����ի@�ֺ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Փ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M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˹���x�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Σ����S�r���܉�����һ��ʒ�l�đ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q�Q������܌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Ī�^���^���վo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36�긻�m���֡��_˹��(Franklin Roosevelt)�B��֮��㷸���@һ�e�`����c֮�෴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Ҫ�Mһ����ؔ���̼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P��˹���x��***�߂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ؔ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l���ɳ��m֮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Ռ��Ľ���ռGDP��62%����2021���90%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(Carmen Reinhart)�Ϳ���˹���_���(Kenneth Rogoff)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H��Ӱ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ؓ�����^GDP��90%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¸��͵����L���ߵ�ͨÛ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DŽP��˹���x�߂�ָ����10���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ʴ�s��3%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ͨÛ�ֻţ����P��˹���x�߷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ȯ�Ј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ǝu�Mʽ�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|�lһ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{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ȯͶ�Y�߮��ĵ�߀���H�H��ͨ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յĺ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ص�47%�����ړ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Fij�N��ʽ���`�s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P��˹���x�߂��Q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վ��l��(bond vigilante)���Ǔ��L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˹���x�߄t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P��˹���x�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@һ�˔��܉�ؔ���̼��D�Q�ɔ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飬�෴������Ҏģ�������ړp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ʾ��δ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ؔ��ý�w�s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N�Ƕȁ��f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ڽ����W�Ġ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ښvʷ�����_˹��1933�����_�ĕr��ؔ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ռGDP��4.7%���S��1934���_����5.6%�ķ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ڵ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𱬰lǰϦ�������ؓ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ʩ�����2007���ԁ���ؔ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ڑ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õ����θ��ӽ�40�������30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
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l�ۑ𠎂�ȯ�ć��ȃ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r���֫@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ؔ���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ԝMؓ���\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Ҍ�˽�˲��T��ʩ���S��ܿش�ʩ����ֹͨÛ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ڑ�r�ij���Ҏģ�s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߶���ه�������ߵĕr�����ͬ�r����̎���_�Š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ؔ���̼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Ї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^ʣ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s���{Ҫ����ͨÛ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ô�vʷ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ƵĽY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Ȼ�С��ڄP��˹�����ܾ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͢��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ԇ��ں�ƽ�r�ڴ�Ҏģ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܉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y�x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@Щԇ�ɱ�����ԃɷN��ʽ�Ո����Ҫ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s�^������p�_���Ҫô���Ƚ������ͨÛ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ƣܛ֮�r����ͨÛ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@ôһ�̲��ɱ���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؛�ń����О��|�lͨÛ�A���j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1981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R˹���_����(Thomas Sargent)����һƪ�}�顶�Ĵδ�ͨÛ�ĽK�Y����Փ�ġ��@һՓ�Ŀ������DŽP��˹���x�r����Ĺ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)ʹ���ذl�F��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ͨÛ��ʧ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Ψ��ʩ����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ػ��20���o20�����𠎌����ձ�ը���КW֮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ֻ�й���ġ��w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ͨÛ�A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Щϲ�g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ͯԒ�С���Ů���Ľ����W��δ�Ĕ�ʮ����P���A�ڵĽ����W�о����ЌW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s�r�����W�ұ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Paul Krugman)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Ҳ�ƺ�δ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ڌW��֧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Σ�C�����ČW�g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W�����Pע�ĺ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�{��o�҂��ṩ��һĿ��Ȼ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�ڲ��o�𠎞����ṩ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e�ij���Ҏģ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ڕr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݈����45%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J��δ��1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ܟo���Г���ؔ���x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ĵ��{��Ҳ���L��һ����Ƶđn�]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ί��@�N�ֵ֑�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ؽ���30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N�����w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ǷN���Р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ɹ���ʩ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x��Ҳ���ڴ̼�����֮�g���x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˲��T���ĺ��\��˽�˲��T����֮�g���xһ��